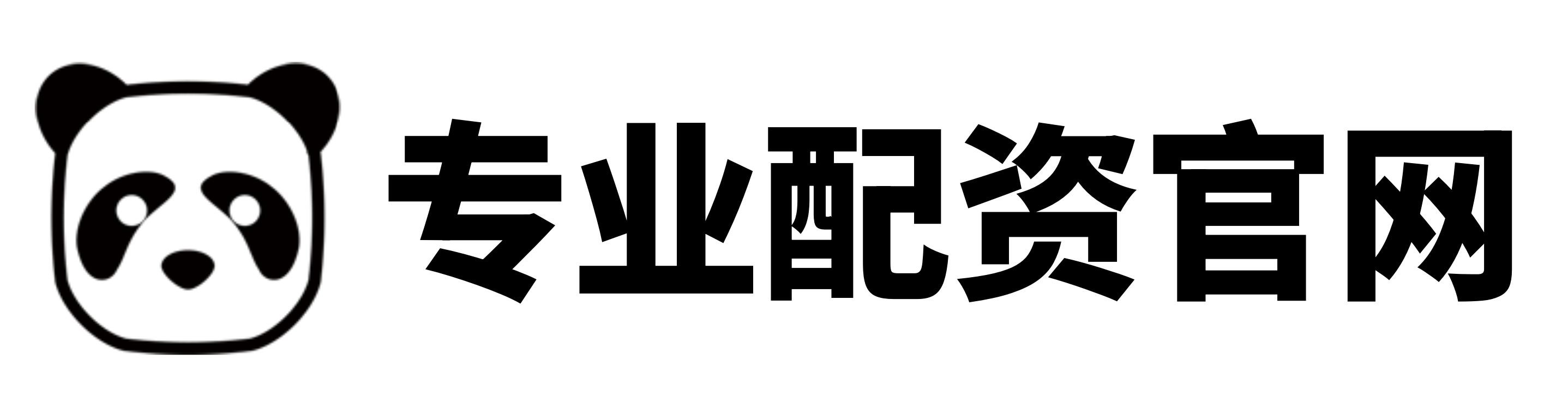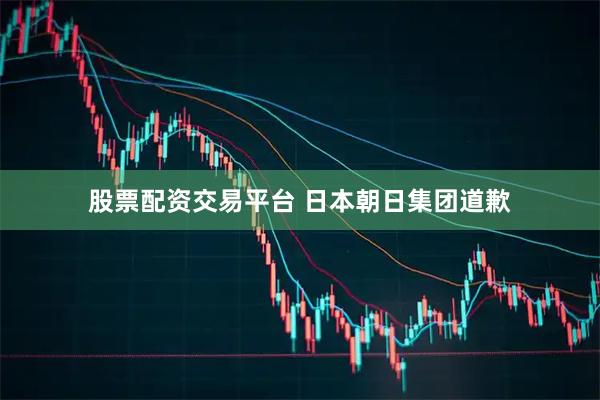股票配资交易平台 帝舜都城之谜:现代科技发现异常,难怪帝尧会禅位于舜_陶寺_遗址_标准

在上个世纪,考古学家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发现了著名的“陶寺遗址”。根据出土的遗物、以及陶寺遗址所处的空间和时间背景,这里似乎正是历史上“尧都平阳”的所在地。根据史书记载,尧帝在即位后将权力传给了舜,而这种平稳的权力交接暗示着两位帝王之间的关系并非遥远。既然尧禅位给舜,那么他们之间的距离应该不远,甚至可能就在同一个地方。否则,尧的帝位怎么可能传给远在山东的舜呢?北魏的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引用了汉末学者应劭的观点股票配资交易平台,认为平阳是尧和舜的共同都城,这也让人联想到舜的都城或许也就在陶寺遗址。
然而,问题随之而来:陶寺遗址是尧族的发源地。如果舜的都城设在陶寺,那么他便有可能侵害尧族的利益。而尧族的其他成员,尤其是尧的儿子丹朱,如何甘心接受这一变化呢?根据清华简《保训》中的记载,以及现代科技的发现,尧的继承者应该是陶寺遗址的丹朱,而舜的都城应该位于距离陶寺不远的周家庄遗址。这一发现也帮助解释了古书中提到的“舜求地中”的记载,并且让我们明白为何尧会将帝位禅让给舜。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晋南地区的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约500座龙山文化遗址,其中以临汾襄汾陶寺遗址和运城绛县周家庄遗址规模最大,都是当时的中心聚落。特别是周家庄遗址,其面积达到了500万平方米,规模堪比陶寺遗址。周家庄遗址的历史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晚期,但其主要特征还是以龙山文化为主。
展开剩余79%距今约4300年至大禹时代的中原地区,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力量便是尧与舜。因此,“尧禅位舜”便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。儒家学派中的观点认为,舜出身贫寒,且缺乏“王侯将相”之类的世家背景,因此他应该是一个强大部落的领袖。这与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帝尧、帝朱(丹朱)有关。那么,周家庄遗址是否可以代表帝舜呢?
周家庄遗址的鼎盛期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,距离陶寺遗址约40公里,位于运城盆地,与陶寺所在的临汾盆地相邻,因此它们几乎处于同一时空。史书中提到,帝舜曾活跃在冀州,春秋时期,运城河津县还存在一个叫“冀国”的地方。古书中提到的“两河间曰冀州”经过现代考证,发现“古冀州”实则位于晋南,涵盖了汾水与黄河之间的地区,恰好包括了周家庄与陶寺遗址。
此外,与舜相关的“虞”国,在商周时期的都城位于今天的山西运城夏县与平陆县一带,距离周家庄遗址也并不遥远。因此,从周家庄遗址的规模、它所处的时空位置,以及“虞国”的历史地理背景来看,陶寺与周家庄遗址很有可能分别代表了史书中的尧与舜。而更为重要的是,现代科技在研究周家庄、陶寺、以及濮阳西水坡遗址时,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殊现象,进一步证明了周家庄遗址可能正是舜的都城。
《清华简·保训》记载了“舜久作小人,亲耕于鬲茅。恐,救中”的故事,其中的“救中”指的是因为“地中”发生了变化,舜需要重新测定“地之中央”,从而确定新的都城。在古代《周礼》中,“地中”被视为理想的政治中心,地理位置代表着政权的合法性。根据《荀子》的记载,“欲近四旁,莫如中央”。因此,作为帝王的舜,选择“地中”作为都城,意味着他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。
在舜担任“小人”时,陶寺遗址显然是当时的政治中心。然而,古文中的“恐,救中”却暗示陶寺遗址已不再符合“地中”的标准。那么,舜作为新帝,理应迁都。而现代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,周家庄遗址的地理位置比陶寺更接近“地中”,因此,舜的都城应该在周家庄遗址。
但问题是,周家庄遗址是否真如预期的那样符合“地中”标准呢?《周礼》中的“地中”标准定义为夏至日中午日影的长度为“尺五寸”,即正午时分的影长为五寸。根据《周髀算经》的记载,尧舜时代的“地中”标准为“一尺六寸”。令人惊讶的是,陶寺遗址发现的木胎漆绘圭尺上,居然有一处突出的第11格刻度,恰好对应了“一尺六寸”的标准。
同时,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500年,考古学家发现了最早的“立表测影”证据。现代技术显示,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°44′50″,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°52′,周家庄遗址则位于北纬35.492085。令人惊讶的是,这三个遗址的纬度几乎相同,说明它们的夏至日影长度也非常接近。陶寺、周家庄与西水坡遗址在地理上的一致性,显然不是巧合,而是有意为之。
由此可见,西水坡遗址在远古时代可能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,许多古代政权可能以此为“地中”标准。而陶寺遗址的夏至日影较长,可能正是“恐,救中”的原因所在。相比之下,周家庄遗址与西水坡的纬度相近,夏至日影更符合“地中”标准,因此舜选择在这里建立都城,也就理所当然。
在今天看来,关于“地中”的理论或许显得荒谬,但在古代,它关乎政权的合法性。从夏商周直到元明,虽然“地中”文化逐渐淡化,但仍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。例如,元朝的都城在北京,但在周朝之后,地中文化依然体现在建立在嵩山的观星台。尧禅位给舜,实际上是政治中心的转移,与双方的权力对比、民心向背以及“地中”标准的契合密切相关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千层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